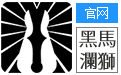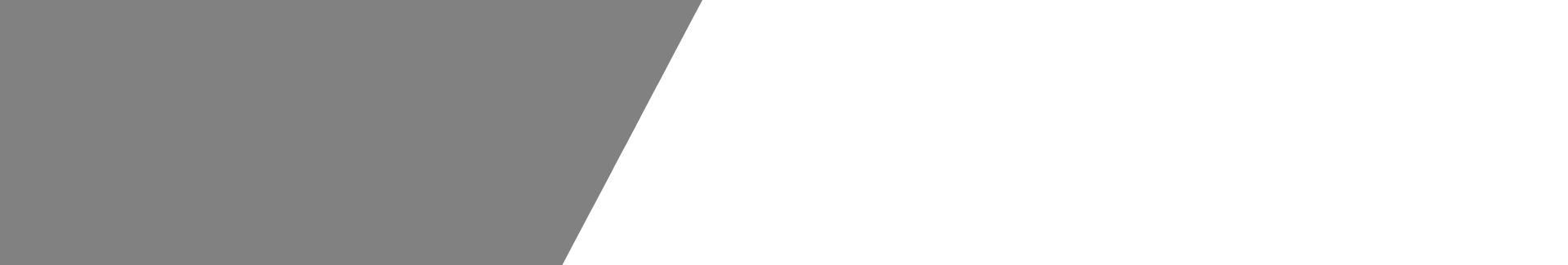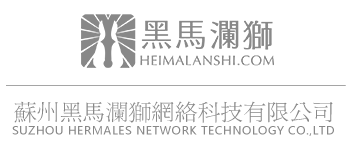这是数年前(2012年)刊载于《纽约客》杂志的一篇旧文。作者在聆听了经管界大师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的一场讲座后,撰文将他在商业创新以及人生思考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。文章颇有价值,不过内容颇长,虎嗅在删减与浓缩的基础上进行了编译。
原文刊载于 New Yorker,原标题为《When Giants Fall》,作者 Larissa MacFarquhar。
“从我现在说话的样子你们就能看出来,以前我中过风。大概……一年半前吧。(好转后)我一直都在重学说话,不过有时,我还是想不出合适的词儿。这个……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眼前这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界思想者抬起眼来,向面前的听众报以歉意的微笑。我记得那天的场景是这样:他站在那儿,身材颀长,双手抄兜,头发偏分并且梳得一丝不苟。他告诉我们,说话时他总想往地上看,因为如果盯着听众,他就会分心。
是的,他就是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(Clayton Christensen),“破坏性技术”理论的首创者。《创新者的窘境》一书就出自他手。

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,图片来自 magazine.byu.edu
像美国许多成功的商界人士一样,克里斯坦森把自身的成功归因于背后的宗教信仰。据说,他在传道授业时就像在教堂证道一样,总追求与受众间心神相通。
今天,面临着诸多商界“信众”,他的这股热情自然也不会稍减半分——当然,由于中风后遗症作祟,他在讲话时不得不把目光寄托于地板,但他承诺仍会尽力而为,将那些谙熟于心的案例,以及他半辈子的发现,再重述一遍。
实际上,《创新者的窘境》问世已经十多年了,书中案例也已经被千万人所熟知。但如今,听众仍然有增无减。大家似乎都认为,这个前有困惑迷局、后有豁然开朗的故事,能救自己于水火。
这着实让他满心感恩。
再讲一遍钢铁的故事
那天面对着听众,他按下遥控器,调出了第一张幻灯片。
“还是以钢铁业为例吧。历史证明,人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让自己成为钢铁大王,”他说,“一是开大规模综合型钢铁公司、下设大型钢铁厂——全球大部分钢铁就是这么来的;二是开小型钢铁厂——只要凑几台小型电熔炉,然后把些废旧金属倒进去就能熔出‘钢’来。最重要的是,这类工厂的生产成本要比大厂低上 20%。好吧,假设你是某大钢铁公司的 CEO,那又怎样呢?年景好时你们的净利润也只有区区 2%-4% 而已。而眼前这个好办法——兴建小钢铁厂,的确能把成本压缩两成,难道,你就不愿一试吗?事实上,还就真没哪家大钢铁公司这么‘开窍’过。而今天,他们十有八九都破产了。所以,为什么某些听起来绝妙的好点子,在聪明人那里就是行不通呢?不是没有原因的。”
这个案例其实是个引子,它引出的其实是克里斯坦森二十年前就开始研究的问题:为什么创业容易守业难?为什么那些人人称羡的所谓大公司,往往只能在成功之巅风光数年,随后便跌落山腰甚至彻底画上句号?
一开始克里斯坦森猜测:这是因为技术在与时俱进,而那些沙场老将们后来都跟不上了。可在深入调查后他发现,事实并非如此。
尽管现代科技在小步快跑和大步跳跃中变得日益精密复杂,但那些老牌公司也不是吃素的——他们大多拥有财力雄厚的研发中心,并且往往一直是同行业技术上的带头大哥。
那为何他们还会中途陨落呢?有些人认为,问题出在糟糕的领导层身上——愚蠢的主管们变得要么谨小慎微、要么夜郎自大,以致无法再做出任何改变。这,就是病根儿了。
但克里斯坦森是位君子,他不肯用“愚蠢”来形容他人。再者,明明是同一位主管,怎么在企业蒸蒸日上时,就被称为天才,而在企业江河日下时就被称为蠢才了呢?其为人行事明明前后如一啊。
问题的答案,或许就藏在钢铁行业的变迁中。那天,克里斯坦森再次抽丝剥茧似的将整个过程拆解了一遍:
“和其他行业一样,钢铁行业的市场也是分层级的,每一层级有每一层级的产品,”他说,“这其中,钢筋是最基础的产品,处于底层市场,而钢板则是制作技艺最复杂的产品,处于顶层市场。一开始,小钢铁厂一味地用废铁炼钢,其产品质量自然低劣得很。肯照应他们生意的,只有钢筋市场的买主们——反正,国家对钢筋没设立任何质量标准,把它们往水泥里一掺,是好是坏谁也看不出来。”
“就这么着,钢筋市场被搅成了一滩浑水。而大型钢铁公司的反应又如何呢?告诉你们吧,能摆脱这个自相残杀的战场,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要知道钢筋这种产品的利润最薄了,与其死守这一市场,干嘛不转移阵地,把资源都集中到利润丰厚远甚的产品上?譬如角钢之类,其利润可达 12%?这么一想,他们就端掉了所有生产线,拔腿走人了——当然,后来利润也就跟着上升了嘛。而钢筋市场,最终成了小钢铁厂们施展拳脚的地方。”
大公司的让位换来了暂时的相安无事,而这种状态在 1979 那一年戛然而止。
“就是在那一年,小钢铁厂全盘获胜,把最后一拨大厂商撵出了钢筋生产领域,”克里斯坦森回忆道,“接着咵嗒一声,钢筋价格直降了 20%。这时小钢铁厂们坐不住了;它们后来的举动证明了一个隐而未现、久被忽略的事实,即:只有在‘高成本对手’与‘低成本对手’处在同一市场层级时,后者所谓的‘低成本战术’才能起效。那么,小钢铁厂们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呢?
这些靠低成本发家的可怜虫们,他们中有人抬头往上级市场瞄了一眼,随后恍然大悟道:‘天哪,原来如此!只要我们也去生产高级钢材,不就又有赚头了吗?’于是他们开了窍,纷纷朝上级市场发动攻势。而那些已经在上级市场安营扎寨了的大公司们,他们这次又会作何反应呢?
没错,和上次一样,他们巴不得再次甩手离开,摆脱这个狗咬狗的是非地——与其死守这样一个利润仅有 12%(又是一个“仅有”)的产品市场,干嘛不去攻占那些利润高达 18% 的产品市场,譬如钢架市场?于是,旧戏又重演了——大公司们果断舍弃了相对贫瘠之地,攀向更高处的肥美市场,其利润也跟着水涨船高。
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,那些尾随者已经快蚕食到他们的脚后跟儿了。许多巨人的倒下,其实从被盯上那一刻就开始了。
这是所有行业大牌们共同的噩梦
其实钢铁行业并不是克里斯坦森研究的头一个对象。在哈佛任职期间,他对有关创新方面的课题燃起了兴趣,当时有人建议他从磁盘驱动器这一行业入手,因为众所周知,该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快得惊人,堪称科技界的“果蝇”(译者注:果蝇孵化速度极快,从卵到成虫只要 10 天左右,一年可以繁殖 30 代)。
果然,克里斯坦森后来发现:14 英寸的驱动器很快便被 8 英寸的取而代之,接着 8 英寸的驱动器又很快让位于 5.25 英寸的迷你新一代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这种更替分明是一种退化。譬如,无论在存储空间还是在每兆字节成本(cost per megabyte)上,后一代驱动器都要落后于前代。
后来,从驱动器行业延伸开去,克里斯坦森又逐一观察了其他行业。结果他发现,这真是一个普遍规律:那些把老牌大公司撂倒的所谓新技术,其实并不比老技术更先进、更优越;相反,它们是一种倒退。自然而然地,利用它们生产出的产品也是低端、拙劣……总之从头到脚都比老产品逊色。
按道理说,老顾客们不应该对次品动心的——有什么理由呢?他们明明有更优质的产品可用啊。但别忘了,新产品往往更廉价、更易用。结果后来,那些不太有钱又不甚精明的消费者们就转向后者的柜台了。而这类消费者——亦即我们所谓的中低端阶层,其人数可比所谓的精英阶层多多了。
也就是在这类消费者的喂养下,那些生产新品(即次品)的公司就昌盛起来了。
索尼就是这么发达起来的。克里斯坦森记得,这家日本公司是在 1950 年代将晶体管收音机推向美国市场的。当然,初代产品糟透了,根本无法媲美当时中产阶级们钟爱的 RCA 或者 Zenith ,但它却在充斥着青少年消费者的底层市场上大获成功。
对这群人来说,所谓 RCA 和 Zenith 都可望不可及,而索尼却意味着“聊胜于无”。攻下这群人后,索尼果然有了本钱。它慢慢地改进其产品,并成功吸引了成年消费者的目光。
最终,RCA 和 Zenith 被索尼远远甩在后面,只能望其项背了。
后来,照相手机重复了索尼的发家史——初代产品的拍照质量糟糕透顶,但因为使用方便,所以很快就遍地开花;站稳脚跟后,其性能自然也就日益优越了。
难怪,克里斯坦森要将这类产品称为“破坏性技术产品”。因为技术本应沿着持续向好的过程发展,但这种产品却把这一过程打破了。
克里斯坦森并非不能理解那些中低端消费者,因为他自己就曾是其中一员。出身贫寒的他,一度靠给快餐店回收废纸来补贴家用。
一辆 1986 年的雪佛兰诺瓦,他凑合着开了好多年——尽管一蜷进去就要忍受车顶对头皮的“按摩”,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小撮头发滑稽地坚挺在那儿,他还是没有轻易放弃这辆坐骑。
此外在家里,他也看不得“浪费”食物。饭菜哪怕再馊再坏,他也会照样包圆儿——这是他的原则。
所以,如果说有什么人会举双手拥护那些廉价但劣质的商品,那说的就是曾经的他了。
同时,克里斯坦森也并不苛责那些逐利而动的大公司。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年增长率,因此对他们而言:第一,依赖低利润产品十有八九是下策;第二,冒险闯入某一陌生市场也似为不智之举,因为万一不幸,等待他们的就是破产。
在他们看来,稳妥之路无非有两条:一、转攻高利润产品;二、冷眼旁观,按兵不动,直等到某一全新市场彻底明晰、或者膨胀到足够令人动心时再下手。